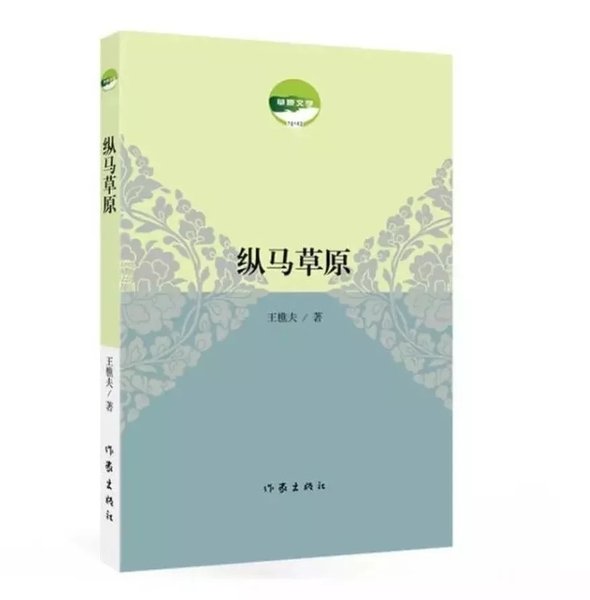
对待草原,欣赏容易,写出它的美却太难。作家王樵夫并非牧人,也不是蒙古族,但他似乎对牧区生活了如指掌。他新近出版的散文集《纵马草原》,不仅透露着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也展现作者宽厚的生命情怀。全书以马为主要叙述对象,分为两章,第一章写人与马的故事,第二章写马与马、与万物的故事。细腻的情感,多样的叙事手法,丰富的内容,详实的材料,让马的故事洋溢着浪漫与深沉。读了这本书,不仅相当于读了一本关于马的百科全书,更是一本马的灵魂图谱。
王樵夫的语言,来自万物花开的声音,有其特有的诗性,在散文中间形成了独特的散文诗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灵性,二是钝性。两个方面截然不同,但都被他所吸收、包容并融汇。他的语言可以游走在名山大川,也可以穿行于草木森林,可以点染沉寂的土地,可以与马和羊对话,也可以像雕塑一样静静伫立并守望着远去的牧人。
灵性来源于何处?我觉得至少有几个方面,一是作家自身的文学素养。王樵夫是比较成熟的作家,涉猎各门类,写过诗、散文、小说、剧本、报告文学,各文体的对话会逐渐培育成对语言的敏感。当然,不同文类的涉猎会不会产生碰撞和内耗,这也是他必须要面对和消化的矛盾。
二是书写对象散发的浪漫。他写的是贡格尔草原上的一群人和一群马,听起来就如此浪漫。贡格尔草原的名气比不了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草原,但有其独特的人文回忆:它位于克什克腾旗这一风水宝地的西部,好山好水美景美人尽出于此。这块小地方,曾经向元帝国贡献了数位皇后,只要稍微定定神,我们就不难想象出游走在这片草原上的迎亲队伍之浩荡。这儿也是灵物的沃土。王樵夫写的马,既有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马共同的特点:俊美、飘逸,奔跑起来如闪电一般。趟过草原的河,溅起的水花和马远去的背影正好形成了一出水幕电影的构图。但这马还有不同之处,它是蒙古马。蒙古马的外形并不出众,精神特质却更为突出,与人的关系也最为紧密,不仅是牧人家中的一员,也是蒙古文明浮沉之间的见证者。作者为写好蒙古马的生活,做了大量的案头与田野工作,不仅写透了马的状貌、生存境遇,甚至还悟透了马的伦理,马的喜怒哀乐。
当然,如果只写马,充其量也就是一本马的图谱,或者是数篇马的童话。但作者的雄心又不只在于此,他深入挖掘马的生活背后人的生活,马的精神背后人的精神,马的文化背后人的文化。每一匹蒙古马的背后,都立着一个蒙古人,或者一个蒙古家庭。蒙古人有什么精神,蒙古马就有什么精神。蒙古人有什么气质,蒙古马就有什么气质。王樵夫笔下的牧人和马在现代社会面前,也许并不老练,但他们一旦回到了自己的草场,就是那么潇洒,那么率性,那么快乐。
第三,体现了作家的世界观。一个作家的世界观有多辽远,他笔下的文字的生命质感和力度才能有多瞩目,他把更多的热望投给了马和人背后的世界。
当前,虚构与非虚构的不断碰撞正引起作家、学者浓厚的兴趣。实际上,王樵夫的写作既是又一次碰撞,也是一次真正的融合。他的散文有大处的真实,也有小处的虚构。像小说,也像诗,更像与马、牧人和草原对话的大戏。但他并没有痴迷于技艺,而是更多向世人展示他心灵的真实,真正把世界观给了世界。写马和人,其实就在表达他对世界的看法。
他语言的另一特质是钝性。妙处在于此:作为一个较为成熟的作家,他却始终坚持以朴拙的方式表达情感。用极简的语言,去除冗杂修饰,直抵事物本质。追求语言的钝性,就是寻求一种极简的艺术,就是讲求摆脱语言的修辞,从而达到心灵的自由。
王樵夫钝性的文字与笔下的生活相得益彰。我不怀疑他可以把散文写得更漂亮,但他始终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以及怎么去写他们。他笔下的蒙古马和蒙古人,都被他塑造成内心柔软、细腻、浪漫,但又不善言辞的一群生灵。
总之,灵性和钝性,这是语言和文学的双重辩证法:过度追求灵性,则难以稳固情感的根基。过度伪装钝性,则有“东施效颦”之嫌。只有在灵性和钝性之间权衡周旋,才能尽取得意之处。《纵马草原》并非无可挑剔,由于题材的唯一性,导致表达方式和情感指向也都存在难以克服的重复,语言也因此受累。另外,散文固定的写作套路还是一定程度限制了作家的发挥,有理由期待,若是王樵夫继续挖掘并扩张某一个故事,会成为非常优秀的长篇小说。瑕不掩瑜,《纵马草原》不仅拥有灵性和钝性的语言,还拥有让人翻江倒海的情感旋流。作家压抑住内心激情而冷静叙事的“中性”指涉,堪称语言杰作,王樵夫也正是草原上那个“只身打马过草原”的过客与归人。
(编辑:张雪娥)
最新新闻







 zgmzzjw@sina.com
zgmzzjw@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