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梵文巴利文专家、印度学家、翻译家黄宝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黄宝生先生一生致力于梵学研究,笔耕不辍,出版专著及译著50余部,涉及印度文学、诗学、宗教、哲学等领域,主要专著有《印度古典诗学》《梵汉诗学比较》《印度古代文学》《〈摩诃婆罗多〉导读》等,以及《梵汉对勘〈入楞伽经〉》《巴汉对勘〈法句经〉》等佛典对勘系列12部,主要译著有《十王子传》等“梵语文学译丛”系列15部、《梵 语诗学论著汇编》(上下册)、《摩诃婆罗多》(全六卷)、《印度哲学》(合译)、《薄伽梵歌》《瑜伽经》《奥义书》《印度佛教史》等,并撰有《梵语文学读本》《梵语佛 经读本》《巴利语读本》《罗怙世系》等梵巴语系列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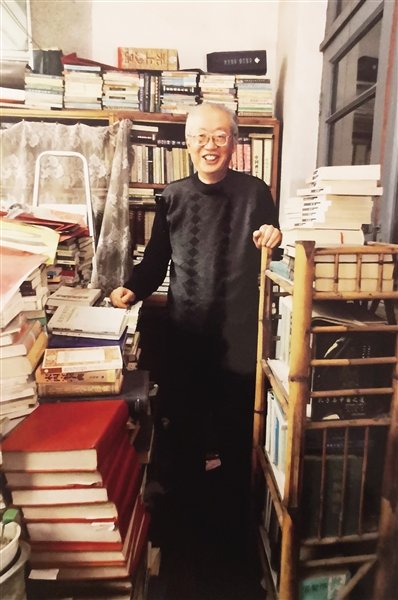
黄宝生先生在家中阳台上。
人物小传
黄宝生,1942年7月25日出生于上海,1960-196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师从季羡林、金克木研习梵文和巴利文;1965年毕业,入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曾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梵文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曾获印度总统奖(2012)、印度莲花奖(2015)、第22届师利旃陀罗塞迦罗因陀罗·娑罗私婆底国民杰出成就国际学者奖(2019)、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23)等。
上世纪60年代初,怀着一颗激荡的心,黄宝生走上梵学之路,这一走就是一个甲子。60多年来,他矢志不渝地行走在将古印度智慧纳入中国的路途中,成绩斐然,梵学成果逾千万言。
在梵学研究中,翻译不仅对学术研究有辅助作用,更是重要的研究工作。用时人之语对前人典籍进行注释、翻译,便于时人与后人理解,其佳者也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对于翻译的格外侧重和翻译与研究的有机结合,是黄宝生学术研究的重要特点。他曾说,翻译是一种最好的精读。精读有助于加深理解,理解的过程也就是研究的过程。翻译和研究,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古印度智慧蕴涵着东方的哲思,从古代僧人译经弘法到近现代学术交汇繁荣,对中国和世界都影响深远。“刹那生灭”“镜花水月”,这些异域的思想以其生动的意象和口语化的特征伴随佛教传入中国,而这种“旅程”让不少人甚至没有感知到它们的源头。阅读上千年前的梵语文献,因文化迥异、语言艰深而难度倍增——疏通晦涩环节,提供完整译文,用现代汉语精微阐释,加之以系统研究,其价值不言而喻。
经过几代梵文学者的努力,梵文原典的汉译本已初具规模。《五卷书》《本生经》《故事海》是古代印度最著名的三部故事集。季羡林译出《五卷书》全本;黄宝生与夫人郭良鋆合译出《佛本生故事选》和《故事海选》。季羡林译出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优哩婆湿》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黄宝生译出跋娑的剧本《惊梦记》,并主持翻译了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金克木翻译了迦梨陀娑的抒情长诗《云使》,黄宝生译出了迦梨陀娑的长篇叙事诗《罗怙世系》、抒情短诗集《六季杂咏》,檀丁富于传奇色彩的长篇小说《十王子传》,以及随后收入“梵语文学译丛”的十余种著作。2008年,黄宝生还汇集10部梵语诗学名著(6部全译,4部选译),出版《梵语诗学论著汇编》,又于2019年出版了增订本(8部全译,2部选译)。黄宝生翻译的梵文、巴利文原典,绝大部分是国内的首个译本和唯一译本。
《摩诃婆罗多》卷帙浩繁,令许多西方学者望而却步,至今也未能出版精校本的英译全本。西方学者深知,对于一个梵文学者来说,必须有了充分的学养积累之后,才能着手翻译《摩诃婆罗多》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也就是说,一个梵文学者决定翻译《摩诃婆罗多》,就意味着要为它奉献自己一生中的学术成熟期。从1996年到2005年的10年时间,黄宝生夜以继日地工作,完成了这部书绝大部分内容的翻译,还承担了全书译文的校订和统稿工作。那些年,他“常常是夜半搁笔入睡后,梦中还在进行翻译”,将生活中的一切置之度外,如同进入“学问禅”(黄宝生《〈摩诃婆罗多〉译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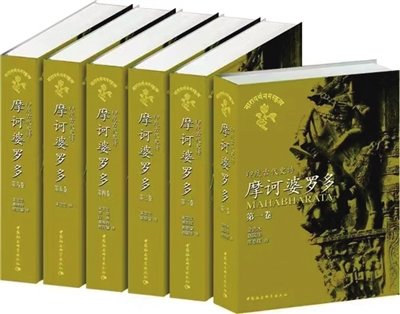
黄宝生译著《摩诃婆罗多》
《奥义书》在印度古代思想史上地位举足轻重,是六派哲学的源头,也是印度上古思想转型的关键著作。文学作品离不开哲学思想。黄宝生在《宗教和理性》中说:印度原始宗教中颂神诗与巫术诗相融,宗教神话发达;奥义书时期探讨终极真实、世界本源,体现思辨理性,开印度哲学先河。中国上古时代亦是巫史并称,之后由儒家体现实用理性,道家、玄学和名辩学体现思辨理性,道教和佛教分担宗教信仰。17世纪,《奥义书》被译成波斯文。19世纪初,法国学者迪佩隆依据波斯文译本,将《奥义书》翻译成拉丁文。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读到这个译本,颇为受益。可以说,《奥义书》的西文译本影响了西方现代哲学。黄宝生提供的《奥义书》汉译本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印度宗教哲学的发展历程,也为中国学术界注入了新的灵感。
黄宝生对于翻译的强调,不仅是站在学术价值和学术规范的角度,还有他作为一位中国学者的坚持——立足中国。研究古印度,正是为了充实中国的学术。
在翻译的基础上,黄宝生对印度文学、梵语诗学、佛学、哲学、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等领域都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著作当中,1988年初版、2020年增订再版的《印度古代文学》和1993年初版、2020年收入“东方文化集成”的《印度古典诗学》是国内印度文学专业的必读书;《〈摩诃婆罗多〉导读》汇集《摩诃婆罗多》汉译全本中的导言、后记和4篇研究文章,是《摩诃婆罗多》研究的开山之作。2021年,黄宝生将多年的梵学积累汇聚成一部专著《梵汉诗学比较》,是中国比较诗学领域一部难能可贵的力作。
2011年起陆续出版的“梵汉佛经对勘丛书”,是黄宝生在梵语佛经的翻译与研究工作中的巨大贡献。《入楞伽经》传入中国后,不仅成为唯识宗的重要经典,而且催生了禅宗。中国禅宗中的渐修和顿悟说与《入楞伽经》中的渐次和顿时说有直接关联。《入楞伽经》前后4译,现存3种,即求那跋陀罗、菩提留支、实叉难陀的译本,均有缺瑕。《入菩提行论》在古代印度非常流行,释论有百余种之多,传入我国西藏后备受推崇。《入菩提行论》在中原地区未能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天息灾译本“译文拙劣,错讹甚多”(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严重影响了佛经的流传。黄宝生的对勘研究和今译从根本上弥补了古译的缺憾。《维摩诘所说经》是一部非常重要也相当成熟的大乘佛经,前后7译,现存3种,即支谦、鸠摩罗什、玄奘的译本。黄宝生在对勘过程中详细探讨了鸠摩罗什和玄奘翻译风格的异同,指出鸠摩罗什具有文字简化倾向,玄奘更倾向于逐字逐句译出,必要时还略有增饰。《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和《无量寿优波提舍愿生偈》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根本经典,合称“三经一论”。现存讲述阿弥陀佛净土的佛经梵本有大小两种,鸠摩罗什译《阿弥陀经》和玄奘译《称赞净土佛摄受经》为小本,康僧铠译《无量寿经》等为大本。黄宝生对比什译和奘译风格,指出什译文字简约流丽,奘译倾向求全;康僧铠的大本译文则使用浅近文言,文体风格趋于简约,文字总体水平优于梵本原文。通过梵语原典读解佛经,不仅是中国古代译经活动的延伸,也是现代佛学研究的必然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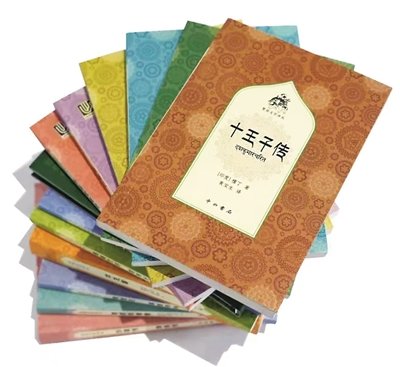
“梵语文学译丛”系列
黄宝生利用梵语佛经抄本或校勘本,对照汉译佛经,厘清经典文本源流,提供现代汉语译本,有助于把握印度佛教的原始形态;有助于研究汉译佛典,阐明佛教义理;有助于读解梵语佛经,校勘写本文献;有助于研究佛教汉语和语言哲学;有助于研究佛经翻译史和翻译理论;更有助于深入理解异域文化,发挥中国学者的自身优势,在比较文化领域有所作为。同时,黄宝生还带着文学研究者独到的视角和半个世纪古印度文学文化研究的深刻体验进入佛典,更倾向于把佛教文献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和细读,从而将这些佛教文献的宗教意味稀释为历史文化背景下的隐喻;语言上的优势也为他读解佛典提供了一个更为客观的视角。
黄宝生很关心青年学者的发展。这些年来,在翻译、研究之余,他也在孜孜不倦地培养年轻一代梵文巴利文学者。他说,既然担任梵文研究中心和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的负责人,就要多为国家培养人才。他希望青年学者能够依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发展,发挥各自的长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
《中国民族报》(2023年4月14日 8版)
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zjnews_mzb@163.com

- 前一则: 从敦煌石窟女性供养人像看民族交融
- 后一则: 九项议程多项活动 癸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准备就绪
最新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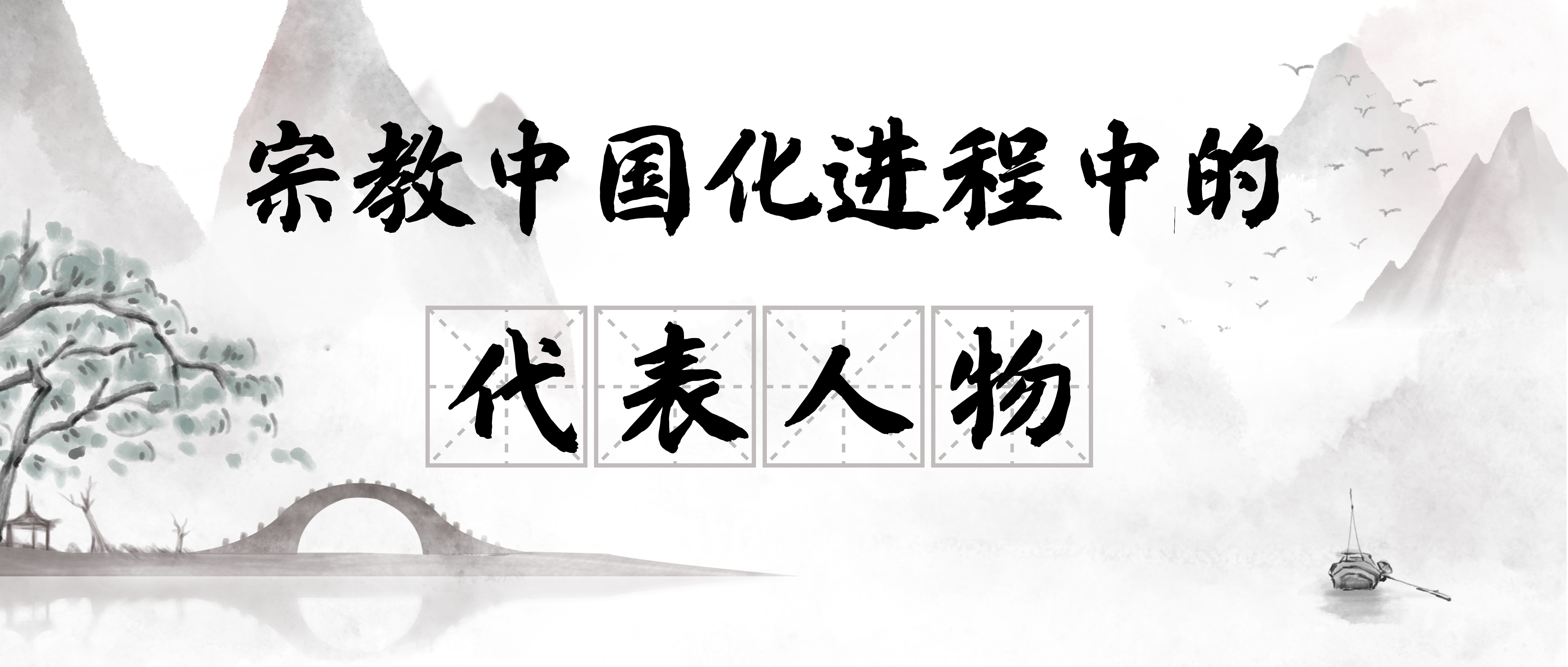

 zgmzzjw@sina.com
zgmzzjw@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