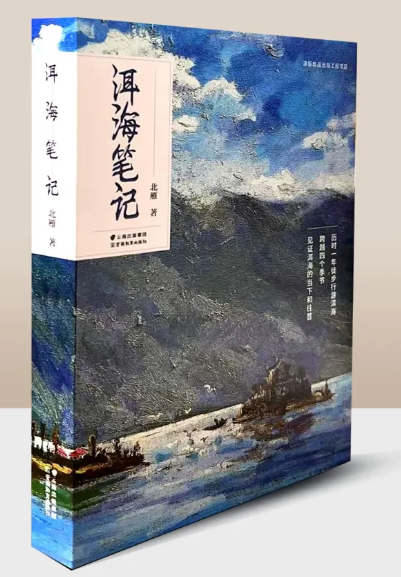
小邑庄其实一点都不小,密集的房舍在两边延续,一条路似乎总走不到头。不多一会儿,太阳落山,天色暗了下来,妻女早已疲惫不堪,坐在路边的木椅上休息,我则决定把村子走完。还好眼前很快出现一条纵贯村落的主路,十字交叉的路心,晚集还没有散。集子东面,一块高大的照壁立在路心的大青树下,上面大书“腾蛟起凤”四字,下面的石栏上,有两三个老人正悠闲地坐着聊天,真是一幅动人的黄昏晚景图。
在大理乡间,照壁一般立在村口或是四合院的朝阳方向,其作用主要在于遮光、后午时分的采光,同时兼有中国传统园林建筑中的“障眼”之效。白族作家、已故云南民族大学教授杨荣昌曾在一篇旧作《白族的照壁》中这样阐述:“照壁一词,以文窥义,许与日照有关。”“清早太阳升起,照壁可以适当地遮挡一些阳光;傍晚太阳西落,照壁便以其自然的漂白给主屋反射一些光亮,亦便于人们的劳动与生活。”
走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老人和一个妇女,领着两个小孩,许是在家里捉儿弄孙折腾了一天,就选在天黑前到达洱海边,散一趟心后就回来休息。两个孩子好似出笼的神兽,步子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息。我加快脚步超过他们,绕过照壁,洱海就到了。湖滨是一块开阔的空地,停满了车。此时前来散心的人还不少。
“在村庄里迷路的时候,你就找一条巷子走到海边,然后就能够看清自己大致到什么位置了!”
和我说话的李老汉实在有些古道热肠。这么多天来,让我始终在心底感激的是,在洱海之畔,我所问到的任何人,无论村妇老人,还是孩童少年,从来就没有过怕羞和矜持的冷场。我想这应该是博大的高原明珠洱海,在数千年相濡以沫的光阴中,赐予当地人民的包容情怀与接纳胸襟。
暮色苍茫。蹲在湖边的李老汉一头白发被落霞映成了金黄色。我估计他有七十岁,果然他说我猜对了,今年古稀有一。说完又笑了笑,“这是整个大理仅次于周城的村子,人口有七八千!”他顿了顿,又说:“其实村庄原本没有这么大,至少在以前是分开的,小时候我们从南往北,村与村之间的距离还有些害怕……”
“怕啥?”
“怕狼!”
“那时有狼?”
“有狼!不光有狼,水边还有湿地、沼泽、芦苇,夜间走路可得留神,否则走到水里都不知道。水边还有各种各样的鸟,白鹭、秧鸡,还有各种鹤类。走着走着,扑通一声,一只大鸟出来,吓你一跳!而且不只天上飞的,还有水里游的,弓鱼、鲢鱼、鲫鱼、鲤鱼,那滋味别提有多鲜了……”
李老汉说着连自己都开始咽口水。看他滔滔不绝的样子,我脑海里居然一下子浮现出多年定居大理下关的满族作家铁栗笔下一个叫作《喧响村庄》的短篇小说里描绘的景况:一个喜欢以洱海为伴的老人,家里房子盖得越来越大,每个家具物件都有摆放的地方,而他自己却不知道该摆哪里了。走出家门,整个村子也都噼里啪啦地笼罩在一种浮躁的建筑声中,只得每天来到村口面对洱海,寻求一个宁静的角落寄放心灵。
我双脚发麻,蹲不住了,起身看着东边一条用石头垒着的水坝伸入洱海,李老汉说那是从前的水路。
“水路?”
“在以前,洱海的水是能直接喝的,家家户户都到湖心挑水喝。坐在船里,我们就用洱海水煮鱼、做饭,回到家里,我们用洱海水泡茶、熬汤……”在他的讲述中,我隐约看到,曾经无数个日暮苍山的夜晚,洱海边上,老老少少在差不多累得散架的时候,就跪在湖边,接着磕头一般把头伸进湖水里,跟水牛一样狂饮;又有多少个日夜,生活在这块神话家园里的洱海子民,把自己极度劳累的身体泡在水里,随波逐流,让一身臭汗和困乏被湖水一点点卸去。
我点开手机搜索,小邑庄隶属于才村行政村,西连古城,东临洱海,辖区有4公里多的洱海湖岸线,是整个村委会最大的自然村。查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大理市地图,标注中只有“小邑庄”,没有“才村”。建筑业的迅速崛起,让小邑庄成为享誉滇西的名字。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几十年间,大理古城80%的建筑均为小邑庄人所建……
天色渐渐黑下来。一群白鹭越过村头的房屋向村后飞去。那个在我前面带孩子来洱海的老人和妇女又把孩子带回村子,孩子们顽皮的欢叫如同天籁。李老汉却没有起身回家的意思。我想他是否就是素以细描著称的铁栗小说里的原型。
看他说得起劲,我只得又重新蹲了下来,过不久感觉脚底发麻,索性一屁股坐到地上,只听李老汉在旁边大声说道:“我听说为了保护洱海,政府准备把湖边50米的房子都拆了,重建海滨与湿地……”
(编辑:魏妙)- 前一则: 《珍爱之地》:多民族互嵌融居的影像散文诗
- 后一则: 对母亲湖的深情告白
最新新闻







 zgmzzjw@sina.com
zgmzzjw@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