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清代在努力推动“大一统”国家建构之际,也在延续“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策略。对于这一点,您在书中说汉地和边疆地区均有体现,请您介绍一下其具体情况?
杨念群:在汉地,清代基本沿用了宋明以来的政治体制,通过科层制官僚和地方精英展开治理。在边疆地区则根据族群和文化的不同,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例如在蒙古实行扎萨克制;在新疆沿用伯克制,保留当地贵族的爵位和称号,但在军事和行政管理上通过军府制加以控制;在西藏则实行政教合一体制,派遣驻藏大臣监控喇嘛制度的运行;在西南采取的是土司制度,一方面推进改土归流,另一方面土司仍具有明显的自主性,并未完全被流官控制和取代。面对着如何统治巨大空间和复杂人群的难题,清代采取“因俗而治”的方式,可以将当地固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整合进“大一统”框架之中,最大限度节约治理成本。
“因俗而治”不等于维持现状的治理术,其关键是在不同文化内部建立起清代统治的“正统性”,形成“大一统”的有机联系。典型的表现是,清代形成了独特的“二元理政模式”。对深受儒家影响的汉地,清帝着力打造“治道合一”的圣王形象,高扬“回向三代”的大旗,以儒家领袖自居,支持宗族、乡约建设,鼓励士人官僚躬行践履、经世济民,展开教养兼施、移风易俗的政治实践,获得了儒家精英的自发认同,使其道统意识和基层“自治”不再成为产生异见的温床,反而成为延展和支持皇权的力量。而在蒙藏等地,统领广阔疆域的清帝被尊为“能向外藩传令”的“转轮王”,成为信众崇拜的对象,使蒙藏地区的活佛体系和社会治理结构统摄在清帝的神圣权威之下、安置在“尊王”的“大一统”布局之中。可以说,在清代,治理层面的“不易其俗”“不易其宜”,是通过正统性上的“修其教”与“齐其政”统合起来的。

▲《乾隆皇帝佛装像唐卡》,故宫博物院馆藏。
清代的“因俗而治”是“大一统”的表现形式,却不是它的本质规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西南地区,清帝便与士人一起,在维持土司传统与施行儒家教化之间灵活游走,并非固守“汉化”或“因俗”,而是以是否利于“大一统”为转移。清代从未放弃国家一体化的努力,不断渗透和改造“蛮夷”,使之逐步“内地化”;这不意味着改变“因俗而治”,而是展现出清廷与地方持续博弈、达成动态均衡的治理形态。“因俗而治”不是单纯强调“分”,而是“寓合于分”“以分为合”,使清代得以有效控制广袤的疆土,并将“大一统”潜移默化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近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记者:在晚清民国之际,革命党人曾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将西方传进来的民族主义观念和大汉族主义观念相结合,以鼓动革命。但在民国建立后,他们又积极提倡“大一统”、并竭力构建五族共和的国家形态,在这样的转变中,是否说明了“大一统”观念的近代转化?请您详细阐释一下其中的基本逻辑。
杨念群:近代中国面对内忧外患,又受到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很快将一度沉寂的种族观念激活起来。但革命党人很快意识到,在民族主义勃兴、列强虎视眈眈的现实局面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必然造成国家分裂的严重后果。故而民国建立后提倡“五族共和”,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各民族生活的地区是中华民国疆域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的诉求应置于中华民族的统一意志之下。此后,“大一统”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日趋同构,成为现代中国进行社会动员、加强民族凝聚力、抵抗外来侵略的支撑点,转化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国家观。

▲中华民国六年黎元洪五族共和纪念币,纪念币上刻有“五族共和”字样。(图片来源:华夏收藏网)
“大一统”观的近代转化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一方面,近代知识分子一度认为专制集权、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偏于静态保守,无法在激烈的文明竞争中占据优势,推崇效法培育公民意识、施行地方自治的欧美经验。但一旦面对救亡图存的政治现实,学者们便极力协调“大一统”观与现代话语,号召打造强有力的统一国家,并通过对《春秋》等古典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诠释,重新为“大一统”和中国政治文化赋予了超越西方弊端的普遍意义。另一方面,人们一度幻想引入西方制度将一劳永逸地解决晚清以来的各种问题。但将包括科举、帝制、经学在内的传统要素一并推倒,打断了乡村与城市、社会与政府的纽带,也瓦解了延续千年的政治、道德和文化共识及其制度构造。民国初年赤裸的权力政治、行政逻辑、治理失效和道德衰败,带来了对其统治合法性的严重怀疑,也引发了重估君主地位、重建政教体系、重审传统价值的深层思考。“大一统”观的回归具有回应近代中国“正统性危机”的性质,也是在西方冲击和中国经验中重建文明主体性和政治文化形态的努力。
就此而言,从晚清到民国,“大一统”观及其实践并未断裂,而是保持着深刻的连续性。也可发现,不论受外来影响有多大,现代中国的建立最终仍基于自身文化和历史的传承。“大一统”观不但营造了清代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更形塑着中国人深层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成为现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不断回访的母题,具有超越具体历史情境的力量和适应性,是贯通理解古今中国政治和文化运作的关键一环。而对于身为现代中国人的我们,在透过“大一统”的深层逻辑理解历史的同时,还需进一步思考,为何“大一统”具有如此强大的制度、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能够收编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行动,且历久而弥新?又应如何看待“大一统”的价值,正确把握它与个人独立和精神自由的关系,在现代世界安置它的位置?只有从当下的情境出发,超越“复古”与“革新”的二元分划,才能真正为传统赋予生机,使之超越功利需求和地方性知识的范畴,成为对现代性普遍问题的政治和文化回应,完成“大一统”观的现代转化。
受访者简介: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1997)、《杨念群自选集》(2000)、《中层理论》(2001)、《雪域求法记》(合编,2003)、《再造“病人”》(2006)、《何处是“江南”?》(2010)、《五四的另一面》(2019)、《“天命”如何转移》(2022)等,主持《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及“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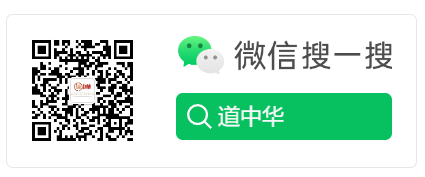
监制 | 杨新华
统筹 | 刘佳 胡俊 康坤全
采写 | 薄辉龙 吕飞跃
编辑 | 郭晖
制作 | 胡琪
(编辑:马永)
最新新闻




 zgmzzjw@sina.com
zgmzzjw@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