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方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平等观。那么,“宗教适应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也有渊源呢?我发现荀子的无神论就是能够尊重他者宗教信仰的无神论,从社会管理的高度看到鬼神之道 (古代的宗教)有道德教化功能。中国历朝实行宗教包容政策从而形成宗教文化多元通和生态与《易传》“神道设教”的思想,与荀子以恕道对待民间鬼神习俗的思想有密切关系。

牟钟鉴
学人小传
牟钟鉴,1939年出生于山东烟台,中国哲学史、宗教学专家。1957年至196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任继愈、朱伯崑诸教授,1966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1987年调入中央民族大学。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宗教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山东尼山圣源书院荣誉院长。牟钟鉴先生以渊博的学识教授人、以高尚的道德感染人,不仅培养了40多位宗教学和中国哲学领域的硕士、博士毕业生,而且带出了一支思想政治坚定、学风优良、善于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队伍。
牟钟鉴先生长年涵泳儒学、探索道教文化、提倡文明对话,在儒学、道家、道教、佛教、宗教学、中国哲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了《<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中国宗教通史》(与张践合著)《中国道教》《走近中国精神》《儒学价值的新探索》《老子新说》《概说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与吕大吉合著)《当代中国特色宗教学十二论》《新仁学构想》《道家和道教论稿》《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荀学新论》等。在这些著作中,先生提出的 “宗法性传统宗教”“民族宗教学”“新仁学构想”,以及中华文化“多元通和模式”等一系列具有原创意义的学术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牟钟鉴先生致力于研究传统文化对当代生活的价值引领作用,对于传统文化,强调返本开新、综合创新、推陈出新。他研究中国哲学带着强烈的现实关切,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力图把历史与当代贯通起来,使中国哲学具有真实的活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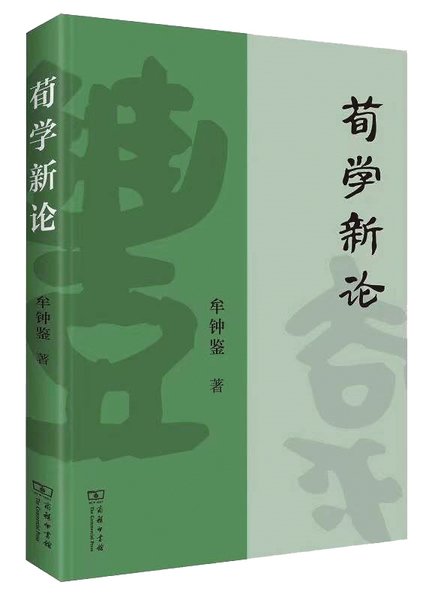
作者:牟钟鉴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1年11月
在新近出版的《荀学新论》中,牟钟鉴先生指出,战国末期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荀子是无鬼神论者,但他对鬼神之道的态度是温和的、包容的,开创了儒家理性主义宗教观的传统,形成治国理政以神道设教为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方略,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
从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到孔孟以人本会通宗教
夏商两代,尤其是商代,中国是一个政权与神权合一的国家,那时最高的神权掌握在君王手中,执政者用天神、祖灵、百鬼来论证中央政权合法性;但从西周开始到春秋时期,中国兴起人文主义思潮,出现第一次启蒙运动,有了初步的理性觉醒。表现之一是殷周之际形成的《易经》,经过《易传》的诠释,从占卜术转化为阴阳之道的哲学,用人事的变化来解说吉凶,迷信的成分大大减少,《易传》还提出了“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卦·彖传》);表现之二是强调天帝的意志要通过民众的意愿来表达,如:“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表现之三是以德辅天,用德治来限制王权和神权,故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尚书·蔡仲之命》)。春秋时期,无神论思想产生,如郑国贤相子产不同意用国宝祭神禳灾,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左传》昭公十八年);随国大夫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把敬神放到重民的附属地位;稍后的周太史史嚣说:“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史嚣又进了一步,他认为神是明智、正直、爱民的,统治者不修其德,只一味迷信祭神,神也不会帮助他,这就把神道归结为人道了。
到了春秋末年,以人本主义为主导的儒家成为显学,其总的趋势是在不否定神道有一定作用的同时,强调人间性,对鬼神之道和死后问题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而把注意力用在阐扬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的修身治国之道上。孔子对于上天既敬而畏之,又亲而顺之,“天”对于孔子,主要是义理之天、生生之天和命运之天,而意志之天的色彩很淡,故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人在宇宙中是渺小的,应当对大自然的力量和社会力量有所敬畏,如此便不会轻举妄动,但不能消极无所作为,而应“尽人事而后听天命”。孔子把人事分成两种:一种是做君子还是做小人完全是个人的事,“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另一种是寿夭、富贫贵贱与理想事业的成败,个人应积极作为,但最终结果只能由天命决定。孔子平日不讲鬼神之道:“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不讲彼岸,主讲人事:“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但是孔子又很重视祭祖和丧葬之礼, 认为它能起到培植感恩之情和推动道德教化的作用,故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子张曰:“祭思敬,丧思哀”(《论语·子张》);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孔子不热心于神道,但对于民间祭祀神灵之礼采取尊敬的态度,因为神道是教化人心的重要方式。由此可知,孔子宗教观的着眼点不在于从知识层面上考察神道是否真实,而在于从信仰层面上看神道(即古代敬天法祖教)所具有的道德功能;他不是单凭个人的好恶而是从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上来判定一种与心理相关的文化现象的价值,这是他高明的地方。孔子对天命鬼神的持中态度,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性格,主流意识既不热衷于宗教,又不排斥宗教并能包纳宗教。这使得中国两千多年间没有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治国以人本为主, 又能用人本去会通宗教,包括各种本土与外来宗教。
孟子继承孔子,对于天命采取敬畏和积极顺应的态度,认为上天降任仁人志士,自己担负着拯救天下于乱世而达到平治的任务,故说:“故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在孟子心中,“天”是融合意志之天、道德之天、命运之天为一体的,其中道德之天是主轴;天与人以“诚”相通:“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后来儒家主流派以道德论天,便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程颢《二程遗书·识仁篇》)。天与人既然皆具德性,那么也可以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人若想知天事天必须从扩充良心做起:“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还将天命与民本相结合,强调天命顺从民意,圣王有天下是天之所授,从民意中即可窥知天意。如万章问,舜有天下,是否意志之天谆谆命之,孟子说“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使之主祭, 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孟子·万章上》)。
荀子开创了儒家理性主义宗教观的传统
荀子发展了孔子和孟子的人本主义,使之达到明白无含混的无神论的程度,这在儒学史上是第一次。同时,荀子又继承发扬了孔子、孟子神道设教的思想,使儒家无神论不脱离神道设教的主线,具有温和理性色彩,并有更为充实的论述。荀子宗教观和无神论的主要观点见于《荀子·天论》和《荀子·礼论》,其他篇章亦有所论及, 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确认天的客观性和规律性
天是自然之天,没有意志,没有道德意识,不是人间的主宰,而是社会生存的自然环境,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它影响人的生活,人应当认识其规律并加以治理,但天与人之间没有神秘的感应关系。《天论》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大自然的变化按自身的规律进行,不会有意给圣王优待,也不会故意给暴君难看;但圣王能够“强本节用”“养备而动时”“修道而不二”,克服水旱、寒暑、怪异带来的灾祸,使社会富足安宁;而暴君却“本荒而用侈”“养略而动罕(少储备而怠惰)”“倍(背)道而妄行”,故有灾荒、疾疫、凶险;因此,乱世“受时(面临的天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最明事理的人) 矣”。
荀子“明于天人之分”并非说天与人不相关,而是说天与人既有关系也有分别,各有自己的路数;人不应消极地听任天的支配,而应积极加以应对,利用自然,减少灾害;社会的治乱兴衰是人为的结果,不能把乱世归结为大自然的原因(不能怨天),要从社会自身找原因。这种天人关系论既是理性的又是积极的。“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人能制驭天时,利用地财,实现社会治世,天、地、人三者可以并列而互动,可见人的能动作用是伟大的;但人的能动作用是建立在“所以参”即明了天地运行规律基础上的,不能一厢情愿。“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大自然的变化与万物的生成发展的更深层的内在动因是无形的,人们难以穷根究底,这就是“神”,并非有什么神灵。可见荀子并不否认大自然的奥秘是人难以窥知的,只是人在理性范围内致力于运用天时地利以达人和就可以了。荀子在意的是社会治乱与天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社会治乱与天、时、地没有关系,做君子还是为小人,也与天、时、地没有关系,这都是人事范围内的事情。可见,荀子明于天人之分,不是为了让人安于现状,恰恰要人担负起做人、做事、治国的责任。他的天人论的宗旨是:“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是很有气魄的高论,表现出一位伟大思想家对人的能动性的高度自信和对天人关系的深邃的辩证思维。
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自然界灾异现象
《天论》说:“星队(流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同‘傥’,偶然)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同时出现),无伤也;上暗初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物之已至者,人祅则可畏也:楛耕(粗耕)伤稼,耘耨失薉(收成不好),政险失民,田薉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祅;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祅。”所谓灾异不过是自然现象中的少见者,只要政治清明,并无危害;一般民间所传的“人祅”,并非真有其事,而最可畏的“人祅”是政险失民造成的灾害与道德混乱,这才是最可怕的。“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文饰)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雩”是天旱求雨拜雨神的仪式,荀子认为这是一种徒劳的迷信活动,与下不下雨无关;日月食而祈祷、干旱求雨、卜筮决定大事,并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它只是民众应对灾异的一种文饰(即是文化)现象,可以缓解精神焦虑,满足民众的心理需求,丰富民间的文化生活。对于明智的君子而言,可视这些求神活动为民间文化而给予包容,并加以引导;对于百姓而言,他们是真心实意相信有神灵的,如果一味相信神灵保佑而不去采取应对灾害的措施,那便会真的引来祸患了。荀子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类似“宗教是文化”的概念,是了不起的,同时也提醒管理者不要使这些民间宗教活动影响了生产,他从管理学角度把精英与一般信仰者作了适当区分,为后来执政者超越自身对宗教的看法来处理他者的宗教信仰问题提供了智慧。
敬祭天地先祖是感恩报本
《礼论》讲人不能忘本,时刻意识到自己生命是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故要敬祭天地先祖并谨治丧葬之礼:“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宗族)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这样,祭礼与人礼融为一体,使人念念不忘感恩报本,不如此,人将成为无情义之小人。《礼记》中也有若干篇文,讲祭祀之功用在于报本反始,在于纪念英雄先祖,在于推行道德教化,其文大都出于荀子学派,故其思想与荀子《礼论》相通。《礼论》尤重丧葬之礼,故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能知之。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关于丧葬之礼提出两大观念:一是把丧葬作为人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培养敬爱先辈的忠信之道的必要途径;二是从不同社会阶层来对待丧葬之礼,圣人明了它的来源和意义,士君子心安理得地践行它,各级官吏用它来稳定秩序,老百姓则形成神道礼俗。如此明白地从社会管理角度谈论丧葬之礼的在先秦只有荀子及其学派,它超出了某一群体的视野,尤其超出了执政者和精英阶层自身观念的局限性,对于丧葬之礼在民间神道化俗中的社会功能有理性的认知,给予充分的尊重,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温和无神论。从古到今,凡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包括当代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都把国家政治运作与宗教活动相分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同群体的不同宗教都能合法存在,不强求信仰一律,但都必须遵守法律,也有益于道德建设。荀子神道化俗观本质上正是如此。
揭示神鬼观念产生的认识根源
《荀子·解蔽》说:“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则未可定然否也。冥冥(昏暗夜色)而行者,见寝石以为伏虎也,见植林以为后(立)人也,冥冥蔽其明也”,“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见其影,以为伏鬼也;卬(仰)视其发,以为立魅(妖怪)也;背(转身)而走,比至其家,失气(气绝)而死,岂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间疑玄之时正(定)之。此人之所以无有而有无(以有为无、以无为有)之时也”。中国民间的鬼魅崇拜,重要认识根源和心理根源之一就是不了解一些奇特的现象,尤其在夜色朦胧中行路,心里本来就恐惧,加上有病或醉酒,在恍惚间把感官感知的种种现象当作鬼魅,这就是“恐惧造鬼”之论。
荀子温和又理性的无神论对后世影响最大者当推东汉王充。他著《论衡》,以“疾虚妄”为己任(厌恶虚假不实,反对“空生虚妄之美”,主张“真美”)。其《自然》《物势》主天道自然无为,正是继承了荀子的《天论》。其《订鬼》对鬼神幻觉的分析,受启于荀子的《解蔽》。其《明雩》讲雩祭并无实效却可以神道化俗,直接来源于荀子《天论》。其《解除》批判“衰世好信鬼”,其《卜筮》《辨祟》《讥日》等篇批判世俗各种迷信,与荀子《天论》《非相》《解蔽》相通。《解除》说:“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后,不能不有吉凶;见吉则指以为前时择日之福,见凶则刺以为往者触忌之祸”,“世人无愚智贤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惧信向,不敢抵犯”,“奸书伪文,由此滋生”。他认为,求福之法,“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行尧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灾消灭”。王充虽然不信鬼神,却肯定丧葬之礼,其《薄葬》认为:“夫言死人无知,则臣子倍其君父”,“圣人惧开不孝之源,故不明死人无知之实”,通过祭祀以行教化。其《祭意》说,祭天地、宗庙、社稷、五祀、山川乃礼之常制,“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报功之义也”;社稷五祀之祭,“皆为思其德,不忘其功也”;“宗庙先祖,己之亲也,生时有养亲之道,死亡义不可背,故修祭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神,缘生事死人,有赏功供养之道,故有报恩祀祖之义”。王充总结说:“凡祭祀之义有二:一曰报功,二曰修先;报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他对祭祀的理论解释,既是无神论的,又是纳神道入人道的,在思路上与荀子《礼论》相衔接。
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zjnews_mzb@163.com
(编辑:石建杭)- 前一则: 支持宗教团体和宗教院校加强自身建设
- 后一则: 中国老学通史研究的“纵”与“横”
最新新闻







 zgmzzjw@sina.com
zgmzzjw@sina.com 